《某个男人》剧情介绍
律师城户章良(妻夫木聪 饰)收到来自谷口里枝(安藤樱 饰)女士的委托,她的丈夫“谷口大祐”(洼田正孝 饰)在伐木现场遭遇意外丧命,而常年疏于联系的大祐的哥哥恭一在看到遗像后却说,这不是大祐,而是另一个人。里枝只能委托多年前帮她办理离婚的律师城户帮助调查,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谷口大祐”究竟是谁呢?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愤怒乒乓球特务追杀令致命之吻亲爱的陌生人德翁·科尔:永远是你的儿子小男人遇上大女人饿狼传说:满月杀手坦途内心的幽灵警告标靶我的妻子没有感情神秘洞穴颜值山海经卧虎监狱学警红线俱乐部之冤家路窄伤不起的青春异变狂鼠中国传世经典名剧FAKEMOTION-乒乓球之王-家庭秘密背锅侠摩登情爱第二季公园与游憩第五季悬崖点爱成金雪琉璃嗨友记数码宝贝大冒险:我们的战争游戏!
《某个男人》长篇影评
1 ) 某个男人:可能是你,可能是我。
反正我也曾有过(现在也常有)“要是当时那样选择,或许现在…”或者,“如果现在重新选择去过那样的生活,一定会更踏实开心吧!
”的想法,终归来说,当一帆风顺的生活出现巨大的落差时,就幻想着用另一个自己开启另一段生活,以替换自己现在的不如意的生活。
我明白,这是对现在的身份和生活太过于不满和失望时,自己主动选择的可以让自己内心舒服一些的不多的逃避方式。
这没有什么可耻的,对于走不出生活阴影的人来说,任何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都需要尝试的,可怕的是,既沉浸在失败或痛苦、恐惧的过往中无法自拔,而又不能面对现实重新开始,抑或切割过往重启人生,宝贵的光阴就此荒废,沉重而痛苦的内心愈发苦涩、消沉,人生就此颓废,那个曾经在别人眼中的人面目全非。
既然做了尝试后还是无法释怀内心的恐惧、愤恨,既然不能容忍自己的父亲、家庭和那个叫原诚(不幸的男二好像是叫作这个名字)的人,索性切割掉不堪过往,再度重启人生,就成电影中X先生的选择和再度尝试的自我救赎之路。
他为他的选择付出了努力,也收获了不幸人生中最快乐也最真实的三年时光!
电影用一个极为特殊的事例来对社会现实和现象的折射,它虽像冰山的一角,却也能迫使我们去思考,面对过往的不幸,我们要如何面对?
面对过往,面对现在,面对未来,面对自己,面对他人…,当我们面对这些不幸却无法自救时,选择用另一重身份开启新的人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X先生的选择,我理解、同情,也颇为认可和羡慕、向往。
男主的出现还原了男二选择成为X先生的心路历程,让观影者在解密男二的过往和过去的身份时,也一路体察着他的现实困境和他在困境中的表现、抉择,不过对于“身份”认可,尤其是展现移民身份和内心困境的问题,我自身没啥体会,所以,也没有对男主那条线所折射的社会现象及导演要表达寓意的判断能力。
看了一些影评,觉得别人分析的挺有道理。
一部电影能同时展示两个甚至多个群镜,而且故事完整,隐喻不浅,画面表达,演员表演都很棒,我觉得它是值得一看,也值得反复看的。
2 ) 某某,你好
在陌生软件里,有人询问我的名字,常常回答叫我某某就好。
其实,原本是想说叫某某某,因为那首歌的歌词里唱到:谈恋爱,和某某某。
但后来发现,恋爱已不适用于我了。
那就改叫某某吧,我不是谁,我只是个某某。
望在万千世界里,我是个不被外人在意的某某,蜗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独自安好。
但当被外人关注时,大多数时候,带来的是压力,是虚伪,是束缚……我已经越来越难感觉到人类的美好了,只能在自然里去发掘四季、动植物的变化,寻找一些真诚。
这部披着悬疑外衣的社会伦理片,便是如此吧,但被无形的身份束缚下,还是有一些希望与美好的,希望,同样的人,都能感受到。
3 ) 看完就不羡慕了
大帅哥、律师、不油腻、有正义感有同理心,妻子漂亮、儿子可爱、丈人有钱,怎么看都是无死角的男人perfect天花板啊……只是,总感觉少了些什么…忽然觉得,这人形式上的、外在的、物质上都是满分,就似乎少了点人情味啊…(原谅我),除了陪伴儿子那一段,似乎感受不到丈夫、父亲的爱(是个好的调查人和律师),总是礼貌而缺乏真情的微笑。
他和X对家人的感觉就不太一样,是因为各自追求的东西不同吧。
又或者是他太优秀了,认为这些都是顺其自然、理所应得的吧……但除了下级要拿工资对上头点头哈腰是情理之中外,还有啥是理所应得的咧……和曾经的我很多雷同啊,经历过那些难堪、痛苦和欺骗,才一夜长大,才明白以前认为永恒的,其实只存在于童话里,但生活的框架哪有那么容易打散重组,所以我更倾向于律师只是给自己一个空间去逃避,毕竟在那些过往里,受伤害的并不是自己。
ps那幅画很有意思,人们总是注释(窥探)他人,又不得全貌,往往凭借自己的经验逻辑去揣测,认为才是最痛苦的人,只是谁又会轻易地向别人坦露伤口呢?
4 ) 寻找“自我”
这几个人物都是有关联的:伐木人、律师、一直担心要改姓的小男孩。
安藤樱这个角色是个参与者,也是个观察者。
这三个人代表了三个群体:杀人犯的孩子、在日朝鲜人、人的幼年期。
他们分别面临着罪与罚、异邦民族、游离在成年人主流世界之外,在这些“弱势”心理和社会环境中,如何找到“自我”,为自我找到出路?
这是要回答的问题。
寻找“自我”,寻找“与生俱来”之外的自我,这个命题是所有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需要去面对的。
在这个围墙之外的人,其实是无法理解墙里的人。
比如,安藤樱的角色,再比如拳击馆的陪练,就是问“是不是自杀”那位。
“自杀”也是一种答案,加缪说:“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
当然,在哲学上去讨论这个“自我”的问题,就太深刻了。
但是,没有深度的生活如同行尸走肉。
对于行尸走肉,自杀是最可能的选择,不一定是字面上的,而是在无知中耗尽一生,茫然地走向死亡。
不记得是哪位哲人说过,“自我”只能从与他人交流融合的过程中获得,“自我”是一个人在他人眼中的镜像的总和。
陷入自我困境的人,比如这位杀人犯儿子,拒绝和朋友交流,钻牛角尖,陷入了《罪与罚》的自我困境,这是从他自己个人内部无法解决的矛盾。
其他两位也类似,都拒绝交流。
当然,他们几个人“筑墙”的能力不同,除了孩子可能是认知阶段的问题,其他两人都有意识的“筑墙”,躲避他人和自己。
这是根本问题,即困境中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面对一个无法独自解决的问题。
这种困境只能借助外部工具,要么是心理医生、朋友,要么是自己学习、读书。
其实这些问题,在历史上几乎大部分人都会遇到,而一代一代大量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哲学家,都曾经不厌其烦的讨论过这些话题。
还是那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对了,剧透一点,伐木人(即拳击手、杀人犯儿子)曾经和拳击馆老板透露过心声,结果被老爷爷按在衣柜上揍了几拳。
老爷爷是个明白人,但是表达能力有限,无法替他解开心结。
这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困境,毕竟表达和理解,往往无法契合。
这也是人生固有的一种遗憾吧。
知心人难得。
5 ) 困住自己的还是自己…吧
7.2在看之前会被海报迷惑 故事的主角并不是他而是他她他们 每一个想要重新活着的人 每一个想要抛弃过去为自己造一个新自己的我 如果可以何不去做到 只为逃离 永远地离开 活在世间的人们看似大同小异其实千奇百怪 于此世间才得以一次次的精彩 这么说可能残忍也可能偏激 可是在我看来 虽然好坏常常只是一线之隔 但因之产生的源才是最迷离扑簌的 我们往往忘记来的路看到的只有现在 而已相较而言 律师先生也是一种“那个男人” 是普罗大众的一员 不能逃避不能触碰也不能只是安于现状 有些微妙的事知道了又能怎样 结尾的关于妻子可能有“外遇”的旁敲侧击很有力量 新的烦恼来了 且是会骚扰他以后的以后的 可能会随时间慢慢淡化 可只要想到 那个瞬间大概又是另一个什么的开始吧 我们始终在这样无聊的困顿里拼死循环 不能自己
6 ) 名字可能是假的,人生才是真的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关于身份、歧视与自我认同的故事。
原诚,有一个双手沾满罪恶与鲜血的杀人犯父亲,他嫌恶自己竟然与父亲有着一张太过相似的脸,以至于每次在镜中看到自己的脸都会浑身颤抖,回想起童年那痛苦不堪的经历。
为了摆脱“死刑犯儿子”的身份,他先后换了两个名字,只希望在一个无人知晓其过往的地方尽量平静地度过余生。
如果不是在砍树时意外身亡,他原本可以心想事成,与里枝和儿女一起过着幸福生活吧?
城户,祖先是朝鲜人,在日本经历了三代之后,他加入日本国籍,并认为自己已经成为真正的日本人。
然而,狱中那个老人认出了他的身份,无耻地表达对他,对在日朝鲜人的歧视;由于经济形势严峻,全国范围内,日本人也在抗议外来人口侵占了属于自己的权益。
也许是受到原诚的启发,他也盗用了“谷口大祐”的身份,一个来自某温泉区旅馆老板家的小儿子,将家产留给长兄,自己外出打拼。
以虚假的身份,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真实的人生,这是一种酸楚,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悠人,自他出生后,先后换了几次姓氏。
先跟着生父姓,父母离异后又跟着母亲姓,母亲再婚后又跟着继父姓。
而现在,这个继父究竟是谁竟然成了一个谜,小小的少年悲怆地问母亲:我还要再改几次名?
我到底姓什么?
其实,悠人还是幸运的。
生父抛弃了他,但母亲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继父身份成谜,但由于他特殊的经历,反而给了自己最完整最饱满的父爱。
虽然他短暂的生命中一直在经历离别,但那位只相处了三年九个月的爸爸,给了他最需要的温暖和快乐。
这是一个悬疑故事,令人感动的是当城户律师最终告诉里枝,与你共度三年多时光的是一个很好很善良的人时,里枝释然地哭了。
是的,她值得一个正直善良的男人与她结婚生子,而那个借用谷口大裕身份的男人,哪怕长着一张和父亲一样的脸,依然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7 ) 静水潭深,不愧是囊获众多奖项的最佳影片
一开始以为结局会发展成为人道主义胜利的样子,然而完全没有,社会仍然一如既往的冰冷,身处其中边缘地带的弱势群体只能继续自己舔舐伤口、小心翼翼的隐藏起来生存。
律师的姓氏一定出卖了自己的朝鲜裔身份,面对岳父不礼貌的话语他仍微笑、妻子出轨他忍耐、不愿自己的孩子继续遭受一样的痛苦不愿意再生,本来,光鲜的工作、完美的家庭、善良谦逊又有能力的人设,是他多么用力才为自己打造起来的保护色,然而,一个陌生的监狱老头,见他的第一句话就撕开了他最不愿意暴露的真实:你是个朝鲜人吧。
老头过去一定遇到过想改名字的朝鲜后裔,一定对这个姓熟悉。
安藤樱演的妻子在得知真相后,跟孩子说,还是要改成自己的姓,因为真实的姓氏是老公拼尽全力不想要的姓氏,而且那个真实的姓氏无论是他还是孩子,在面对社会时都是不可承担的重负,可以理解为妻子对丈夫遗志的尊重,也可以理解为社会的铁板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弱小的个人打破,身为一个母亲,她要理智的保护孩子。
影片最后,律师很陌生人谈话,啊歪个楼,妻夫木聪的侧脸要不要那么完美。
手握住杯子的特写,虽然身处那么放松的居酒屋,律师的手却一点都没放松,他小心翼翼的披着谷口的外衣说着自己的心事,一样的假笑、一样的故作从容实则压抑且紧绷。
他一定也想改名换姓重新生活吧,用这个仍然在户籍信息上存活,但却没有对应的人的名字。
然而律师身份是面对大众的,那么容易想改就改吗,真实名字的名片不想拿出来,但日后若在工作场合遇到眼前的这位陌生人,他又该叫什么名字?
至此,虽然现实还那么冰冷让弱势群体仍旧无法自处,但这尖锐的矛盾让观影者感同身受,把每个人都逼到了无法转身的墙角,或者赴死、或者奋起为了生存而反抗而尖叫。
虽然叙事平静、温情,但静水潭深,这是一部尖锐的呼唤社会集体意识改革的影片,日本社会对犯错人的不原谅、全面否定、甚至延续到对后代和相关姓氏的歧视,太过死板教条不通融。
我想起来那个因温泉水未按承诺频率更换、被发现而自杀的社长的新闻,在他谢罪背后,他的家庭和孩子仍在继续承担着社会的谴责和歧视,选择生还是选择死,在如此巨大的社会压力面前,似乎选择死更容易更轻松,哪怕是影片中改名换姓的假“死”。
(啊怪不得日本人那么怕蒙羞,以及自杀率那么高)影片画展是正面倡议:杀人犯不是只有杀人的那一面,激情犯罪之余,也许他是很好的有自己丰富内心世界的人,对“杀人犯”这个不可改变的标签,他们多想辩解。
专家说,即使是杀人犯,他们也能变好。
就像谷口打拳比赛时也会打红了眼,但不否定他的本性那么善良。
从人道主义层面,每个人都需要被全面的看见,而不是被一棍子打死。
另一个律师说,犯罪者的后代总是更容易犯罪,我们真的要思考,是否是这冷冰冰的社会不给他们任何正当的发展空间导致他们或因生存或因反抗而只能走向犯罪。
当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呼吁既往不究全面宽容,毕竟社会的治理需要一些犯错代价来杀一儆百。
社会的宽容,这个度,如何把握。
电影,是从下而上的呼唤。
8 ) 放弃自己成为别人 才能重新生活的人
电影题材挺好的,世界上有着很多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如意的人,比如在一个不幸福的原生家庭里、比如有着惨痛经历的人,他们要想走出这个人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借助他人的姓名,彻底与那个自己说再见。
安藤樱演技真的很好,虽然戏份没有覆盖全片,但是出场时间就会被吸引进去,小七演的也可以,但是差一些爆发戏。
没想到日本人这么排韩,韩国也许经济不如日本发达,但是感觉韩国人活的更加随性一些。
电影节奏有点太慢,正常倍速看着有点困难。
9 ) 电影节奏不快
慢慢讲了一个故事,对于老婆的出轨,男主肯定是深感嘲讽于不屑的吧,甚至有一丝解脱的感觉,结尾放在现实中,不受过往干扰而用新身 份过活的人真的会存在吗,我不太相信,或许,只是我还没抵达人生的断点罢了,结局也很开放,也有可能全是男主的伪装,抛下以前的身份重新开始,最后那张画提醒了男主现实的生活。
10 ) 身份的作用和迷思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非常喜欢,叫做《某个男人》。
其实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对这种概念先行,观影后劲大,能让我想到很多point的片子没有抵抗力。
这确实不是一部全方位完美的公认佳作,这一点从网络评分也能看得出来,但一部文艺作品足够提供观众一个值得深入思考挖掘的点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首先这部电影的主题很明确,就是关于“身份”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无论是法律身份还是社会身份,身份决定了我们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
影片中也提供了多个具备话题点的人物身份,隐藏过去和他人交换身份的佑大,三代在日朝鲜人的男主城户律师,因次子患癌早夭和前夫离婚,又和佑大结婚却再次遭遇佑大意外去世的寡妇里枝,交换身份前作为杀人犯儿子的原诚(佑大),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为我们揭示身份到底有什么用,以及有着什么样的迷思。
身份的作用当然是我们在社会立足的基础,一个人只要活着就必须有一个身份。
因此影片设定了交换身份这样的戏剧矛盾,真正的佑大,和作为杀人犯儿子的原诚为什么要交换身份?
当然是各有目的的。
原诚而是目睹了父亲的杀人场面,因此产生了深重的心理阴影,又因为自己与父亲极其相似的外表而选择一次次伤害自己,而交换身份对于他正是一种与过去告别迎来新生的象征。
真正的佑大作为家里的次子与父兄不睦,在父亲去世后将家庭祖传的温泉旅馆交给哥哥经营之后,和自负且霸道的哥哥继续生活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逃避原生家庭的控制与干预,便是他选择交换身份的动机。
至于影片真正的男主,妻夫木聪扮演的城户律师,人物设定也是非常有意思,第三代在日朝鲜人,归化为日本籍,有漂亮的日本人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似乎境况并不差,但是日本社会无处不在的歧视其实是根本无法忽视的,岳父母有意无意的显露出的男方高攀的意图,妻子出轨,社会闲谈中的杂音。
在他自己,三代生长的土地却好像始终只是外人。
于是片尾,他在酒吧里与人聊天,也冒用起了佑大这个地道“日本人”的身份。
片尾的这个设定可以说是相当巧妙,我个人认为他只是闲谈中的胡诌,但也确实在点名身份的某种作用,因为在一个普遍建立在他人评价的社会之中,你人怎么样不重要,你是什么身份才重要。
就好像你一生行善,做了件错事。
他人的评价恐怕就是:果然就是杀人犯的儿子,不奇怪。
你兢兢业业做好本分,对工作对家庭负责,面对误解,恐怕也是,毕竟是外国人。
就好像片头,原诚(佑大)来到宫崎做一名伐木工人,不善言辞,性格阴郁。
部门的评价是:一个群马县著名温泉旅馆家的二公子怎么会想到来这种地方做伐木工呢?
就好像城户律师在探究交换身份的真相是,大家的普遍反应是,为什么要交换身份呢?
是不是犯了什么大事?
该不会是犯了罪吧。
正因为来自他人的评价如此普遍而且重要,身份,才成为人在人类社会中立足的基石。
法律上的身份是确定你是谁。
而社会身份更多的是在确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刻板印象。
你是谁的儿子,你是谁的丈夫,你是谁的父亲,你是谁的朋友,以及你是不是犯了什么事。
我记忆很深的还有一个情节,里枝的儿子悠人,在原诚(佑大)意外离世后,情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孩子他还不能深刻的理解身份的含义,但也能通过碎片提出自己的疑惑,他问里枝,妈妈,我是不是又要改姓了?
他还问里枝,妈妈,爸爸都去世那么久了,为什么还不立碑?
你看,孩子虽然没有进入社会,不理解身份对于社会人的重要性,但也会因此感到疑惑。
一次次的改姓意味着不停的变换社会身份,先是里枝前夫的儿子。
父母离婚后,改随母姓,又变成里里枝娘家的儿子。
母亲和原诚(佑大)结婚,随佑大姓,又变成了佑大的儿子。
佑大去世,且验证身份冒用,又要面临改回母姓的局面。
但是,但是我们被定义的身份真的就是全部吗?
影片其实用了很多细节去说明并不是这样的。
里枝在最后对城户律师说,其实好像不需要知道真相,毕竟和他相爱,生下女儿,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原诚(佑大)在大阪生活时,在一家拳馆打拳,拳馆的朋友们并没有在意他神秘的过去,即使最后知道了他的父亲是杀人犯,大家还是选择相信他们心目中的原诚(佑大),他是一个温柔善良,只是带着阴郁的性格的好人。
拳馆的朋友在最后听到城户律师确认他不是自杀的之后非常高兴,那是一种看到朋友走出阴影的高兴。
即使是片头,伐木工的部门内有人对原诚(佑大)阴郁的性格说三道四,领导也说,我还是很喜欢他的。
即使是城户律师,带着疑虑去一步步调查原诚(佑大)身份的真相,在越来越了解他,越来越清晰的看到他的整个人生的过程中,情绪的变化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递交调查报告书时,对出言不逊的真正的佑大的哥哥表示强烈的不满。
这正是影片以及导演要传达的精神。
身份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也确实是我们立足的基础。
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人生,归根结底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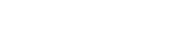




























小成本恶趣味,胜在疯狂玩梗打脸段子够密集,玛丽苏的人生开挂果然有原因,德蒙特莫罗尼贡献出了生涯最佳喜剧演出?
喜欢无厘头
真是一部典型的美国现代主义的烂电影,大概这就是类似于中国的某二代拍出来的吧,这是迄今为止看到的最让你头大的电影,看到一半就吐了
❓
7.9 mary fucking s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