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很危险》剧情介绍
The untitled series, for which he also serves as narrator, will see him take the viewer through a series of vignettes in each episode. The twisted comedic sensibility of his stand-up is the core DNA of this series, where every story will unfold in a in a hilariously disturbing way only he could imagine.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海盗魔童老去和平饭店春光灿烂猪九妹审判葬礼成员金椒花神咖啡馆25时,赤坂见鬼牌游戏厂花动物界国色天香老百姓是天偷听女人心爱的奥特莱斯父亲的菜单欢乐时光谋杀案三叉戟达拉的青春和解在后弗罗拉与松鼠侠鬼屋欢乐送第二季大明悬案录之鉴影篇惊悚机场巴士一山之隔重庆小姐早安秀双生
《思想很危险》长篇影评
1 ) 真正的人生
孩子残疾、失去工作、亲友离世、爱人异地……一家人如何勇敢地追求来之不易的幸福吸引我看了夜间包场电影。
一家四口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和楼下茶馆小姐姐聊到这电影的时候,她说这电影会特别催泪吧,大概是前期足够的心理建设吧,没有哭……电影的跨度十余年,由无数个熟悉生活的场景组成:数次就医、车间工作、陪孩子上课写作业、在串店都不舍得吃、夫妻间的日常争吵……仿佛记录着普通家庭的风风雨雨,两个家庭的不同抉择让命运走向不同的方向……女主美丽而又抗造还有点大大咧咧,男主有点小脾气作为顶梁柱连过年和父母离世时都在卖命工作,在北京住五百块一个月的床铺……女儿的人生几乎是由钉子支持起的,却异常懂事和聪明让人心疼……遭遇了丧女之痛的发小却永远没能走出那暗夜……结局似乎有那么一丝微弱的光亮照进了这一家的生活,女主点燃了之前过年时都没能点燃的焰火(大概一家人在一起才是过年吧)、一家四口一起在路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不完美却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吧……
2 ) 《追幸福的人》
从巧巧(南吉饰)作为北漂母亲照顾罕见病女儿茯苓(吴玉玲珑饰),到因生计被迫返乡、扛起家庭重担的抉择,影片的每一处细节都浸透着生活的粗粝感。
例如,巧巧在农田劳作、深夜照料女儿的场景,既是对底层女性生存状态的精准捕捉,也是对“真实”这一电影本质的回归。
导演祝捷的创作理念——平视而非俯视人物——让影片避免了悲情化或英雄化的叙事陷阱。
通过细腻的生活碎片(如母女间的童言对话、返乡后的家庭琐事),观众得以在平凡中触摸到生命的重量与温度。
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多重困境。
她不仅是母亲、妻子、儿媳,更是一个在生存夹缝中追寻自我价值的独立个体。
面对女儿茯苓的第八次手术、丈夫天冬(梁戟饰)的异地打工,巧巧被迫成为家庭的唯一支柱,这种“被迫全能”的状态,映射了无数底层女性的真实境遇。
影片并未将女性塑造为单纯的牺牲者。
巧巧的坚韧中夹杂着对理想生活的渴望:她尝试融入城市,甚至通过“考一百分就回北京”的承诺,试图为女儿编织希望。
这种复杂性打破了传统“苦情母亲”的刻板形象,展现了女性在逆境中的主体性觉醒。
《追幸福的人》以巧巧一家的遭遇,隐晦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
女儿茯苓的罕见病治疗费用、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打工家庭的分离困境,共同构成了影片的社会底色。
例如,巧巧被迫返乡后,既要应对农村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又要直面医疗与教育资源的匮乏,这种双重压力成为无数流动人口的生存缩影。
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未将社会问题简化为控诉,而是通过人性的微光化解矛盾。
邻居的善意、丈夫的默默付出,乃至巧巧与女儿在课堂上的共同学习,都成为对抗绝望的力量。
这种温和却坚定的叙事,让影片在揭示现实的同时保留了希望的余温演员南吉为角色付出的极致努力——增肥20公斤后又极速瘦身——不仅是对角色外形的还原,更是对“身体作为苦难载体”的隐喻。
镜头下她疲惫的双眼、粗糙的双手,与吴玉玲珑饰演的茯苓纯真却脆弱的形象形成强烈对比,无声诉说着母爱的沉重与坚韧。
在“内卷”与“躺平”交织的当下,影片提供了另一种生存哲学:真正的勇气,不是对抗命运,而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选择前行。
这种精神,恰如巧巧在农田中逆光劳作的剪影,虽不耀眼,却自有穿透黑暗的力量。
3 ) 《追幸福的人》:月光落在未命名时
《追幸福的人》用霓虹与雨水的蒙太奇,解构了当代社会的幸福迷思。
那些被虚焦的日常褶皱里——楼道声控灯的明灭、菜场鱼尾溅起的水珠——藏着比KPI更真实的生命刻度。
当野花从钢筋混凝土里挣出春天,追逐者终于发现,幸福不是待解的方程,而是呼吸间突然停驻的顿悟。
这部城市散文诗最残忍的温柔,在于揭穿我们都在用奔跑的惯性,逃避此刻肩头早已栖满的月光。
4 ) 在逆境中追寻幸福
《追幸福的人》是一部充满温度与力量的现实主义佳作。
影片以罕见病患儿母亲巧巧(南吉 饰)为主角,真实展现了她为家庭奔波于城乡之间的艰辛与坚韧。
导演祝捷用平实克制的镜头语言,将北漂困境、医疗压力等社会议题融入个体命运,情感真挚而不失深度。
南吉的表演极具感染力,她深入原型家庭体验生活,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
影片没有刻意煽情,却以细腻的细节和饱满的情感直击人心,被观众誉为“平凡人的英雄史诗”。
5 ) 何为幸福?为何追逐
片尾响起的时候我恍惚了,随着车厢内镜头向外拉远,巧巧和子苓在车尾放起了烟花,这让我想到了那三颗因为潮湿没放成功的烟花。
多温馨的一幕,但有一个声音在我脑海回响“这生活真的就只能这样下去了吗?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其实这已经是个很好的结局了,映后导演也说了设置这样一个场景,一家人团聚是他们的梦想。
盯着片尾制作人员的字幕眼神逐渐无神,我不知道此刻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复杂到说不清楚。
每个人都在不停追着自己的幸福真实得压抑,都为了活着这个现实问题而奔波劳碌,甚至低头,因而发生了些许事。
全片都不提“爱”却处处都是“爱”,从巧巧第一次怀孕极力保下孩子就可见其爱孩子之重。
林树林的疯也是因为女儿的去世,虽然没有明着说,但我觉得他带走茯苓是真的在教她的过程中对孩子产生了或许怜悯,或许看见了自己女儿的样子,所以去采金莲,也是去见自己的女儿。
对于这个虚构的人物,我还是感兴趣且有许多问题的。
里面的家庭问题,邻里问题,再包括村里的一切都仿佛在照现实的镜子。
再看会巧巧一家,是心酸痛苦的,但为了孩子,什么都得往下咽。
映后影片是把镜头对准女性的,现实的问题,真实的感受,巧巧也年轻过,也有喜欢美丽的时候,她的那一撮蓝色挑染象征着那个不被现实束缚自由的自己,但在林树林死去之后她觉得失去了同伴,失去了有共同话题的人,自己的生活就如此暗淡了,因此她一刀剪断。
其中还多次出现梦和民间传说这类意象,过去的片段不断穿插,慢慢将故事补全。
学校的片段有趣,接地气。
点名婚礼那段,据说剧组是隐藏式拍摄的。
真实是本片的一大特点,但缺点也随之暴露———过于平淡,没有什么起伏。
可以说全片为数不多的高潮是在天冬父母去世后火葬那段,和结尾卡车那段,相同点是都想起了惘闻的配乐,惘闻配乐是电影的点睛之笔,也是因为这一烘托,情绪被推到位了。
电影《追幸福的人》原声音乐7.9惘闻 / 2025配乐摄影方面可以说镜头是美的,不会因为要真实接地气而放弃美感。
真的很喜欢南吉,演绎得非常棒,有种破碎的美感(。
导演在说到惘闻时讲到老谢和他对于电影的创作理念是一致的,所以才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化学反应啊。
加油吧。
据说导演新作仍然有意向和惘闻合作,期待一下。
6 ) 在生活的褶皱里捕捉光
《追幸福的人》,不贩卖苦难,而是以巧巧一家为棱镜,折射出乡土中国最真实的生存韧性——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闪烁的微光,往往比太阳更灼人。
巧巧的追光之路始终在烟火气中延伸。
观众看的不是被生活击垮的弱者,而是用肉身丈量苦难宽度的力量。
那些通常被其他导演用来制造泪点的场景,在这里都成了淬炼生命的砧板,锤打出主人公骨子里的韧劲。
影片的主人公巧巧,懵懂地闯入社会,涉世未深的她很快便承受了生活的重压。
然而,她并没有被生活的不幸打倒,而是始终向阳而生,积极面对一切。
从不得不转学回老家,到安葬公婆,再到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正常教育,最后在丈夫回家小聚后再次出发,巧巧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三次烟花也构成精妙的时间刻度。
每一次都预示着故事的转折。
第一次绚烂绽放在家庭变故的暗夜,第二次伴随同学遇难的闷响,第三次则在短暂团聚后为新的出发照明。
这次不再是团圆与分别的反差,而是积蓄力量后的再次走出山村,这时巧巧手中的烟花格外炫目,也映射她眼中经年累月沉淀出的从容松弛。
婶婶是除了巧巧之外的另一股温情力量。
她先是一路不言语地接回她们母子三人,接着用敲门揭开了春节期间的死亡,最后与侄子、侄媳妇一家难舍难分地告别。
这种乡土中国中最让人感怀的温情力量,多是沉默,但震耳欲聋。
除了婶婶,男教师也在坚守着什么。
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守望着讲台,亲历了几代人走出大山,见证了他们的悲欢离合。
尽管如此,他始终坚信幸福会来,总有希望,并在影片中点出主题:“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虽然周边的人都不那么确信。
整个故事中,大家都渴望积极的变化,哪怕只有一点点。
导演这样讲述脆骨症的故事,既小心又直接。
但他没有让观众陷入单纯的同情,而是引导我们从坚硬可感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各自的奔头。
幸福,就是要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就是用双手去创造,用脚步去追寻。
7 ) 祝幸福的人
影片刚开始其实我是在想,就像巧巧说的那样,如果她没有嫁给天冬,没有生下茯苓,听她堂姐的话,是不是就会好过点。
甚至当我看到茯苓倒在泥潭上时,有一瞬间我觉得这是对她的解脱。
但理解巧巧这个人物就要发现她对家的渴望。
她想要的,可能就是影片结尾一家开开心心的坐在卡车上出行。
我的思想可能是偏向表姐的,我不太能理解巧巧对家庭那种强烈的渴望。
但我又想起那段对话,天冬说自己做了个梦,梦里梦见村子河里的金莲花。
但他却发现自己深陷在泥潭里,而身上的泥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这时堂姐出来说,如果金莲花那么宝贝,那么观音为什么不下来捡。
这时其实就是暗示了两人思想上的分歧。
接着就有巧巧和堂姐都确诊怀孕的情节,但是两人却做了与众不同的抉择。
传说的设定是捡到金莲花的人会获得幸福。
对巧巧和天冬来说,茯苓是降临在他们生活中的幸福,同时茯苓的出现又加剧了他们的贫困,让他们在贫穷这个泥潭里面越陷越深。
影片里有句话,好像是东林说的,他问冬明,你说,我们是不是不配有家。
成家的代价实在过于高昂,一旦决定了就要背上一辈子的债务。
所以堂姐认为这个“金莲花”不是幸福,她认为的幸福可能就像我认同的那样,是就算要成家,那也一定要有面包。
自此,姐妹俩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影片里有提到巧巧对女儿发脾气,说如果没有你们我就过得会有多好多好,其中也提到了堂姐说要开的美容院,这是不是也暗示着堂姐过上了巧巧口中的生活。
会不会堂姐过上了她认为幸福的生活。
导演提到影片里删除了一段后来堂姐的故事,但是却没说具体究竟是什么,这点我还是挺好奇的。
我认为的“金莲花”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这是有侧重的相对的幸福。
所以巧巧在陷入贫困时会后悔,堂姐的分手有没有可能有因堕胎使两人产生了间隙的可能。
那么堂姐独自忍受病痛的折磨时,那几个瞬间她会不会也像巧巧一样后悔。
幸福不意味着完美,它必须有所取舍,而每个人感受幸福的方式又都不一样,但不变的是每个人又都是追幸福的人。
影片中还有一段对金莲花的描写,是林树林对茯苓说的,我要带你去找金莲花,随即他带上茯苓一起去跳河。
对林树林来说,金莲花是什么,是死亡吗?
长久在理智边缘徘徊的林树林在遇到巧巧后,想给她看女儿的照片却找不到。
是不是在那时他意识到女儿确实是死了。
所以当他告诉巧巧他女儿已经死了,而他要去找她女儿,那时候就已经下定了要自杀的决心了吧。
但为什么要带着茯苓一起去死呢?
是觉得茯苓像他女儿还是只是单纯想找个人一起去死。
或者是林树林有点救世主情节,认为活着太过痛苦,只有死亡才能指向幸福,而他看到身患罕见疾病,遭受病痛折磨的茯苓时,想着要去拯救她,让她跟着自己一起走,离开这个残忍的世界。
我还很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是它的真实性。
毕竟导演刚开始是抱着拍纪录片的想法开始的,包括很多素材,取景都很贴合现实。
而在突出这部电影的真实性的同时,影片还加入点浪漫主义色彩,让电影也可以是梦。
比如说最后一个巧巧玩仙女棒的镜头拍的实在太美,令人享受。
看电影的时候,我还有个想法,那就是生命他苦涩如歌,一个人究竟能承受多少苦难。
在一切看似圆满的时候,转角又会遇到措不及防的沉重打击,当你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生活又告诉你,其实你还有可以失去的。
但是当雨过天晴,又总有那么些时候,就像巧巧一家在卡车里的时候,天冬唱着,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开开车,茯苓在一边耐心的纠正的时候,巧巧在车上玩仙女棒,笑的明媚灿烂的时候,我想他们一定是幸福的。
8 ) 追幸福,要像追梦一样有强大的信念感
观影过程中一直在想,这日子也太苦了…后来才了解,电影源自纪录片,里面很多现实困境都是真实存在,这种困境又是结构性的、避之不及的,身在其中的普通人需要执拗的、偏执的坚持,幻想出的美好或许不是解药,却是坚持下去的动力。
记得张沛超老师在分析某个案例时说过,他生活那么苦,不偏执一些怎么走到今天?
就是说,偏执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心理防御,是活下去的手段。
影片中多次表现过“梦”,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偏执的不接受这个现实,倔强的不放弃“追”心底那份幸福。
9 ) 《追幸福的人》:我看到不是一个巧巧,而是一群“巧巧”
——兼论现实主义文艺片的突围与困境 在2025年春天的中国电影市场,一部聚焦罕见病家庭与女性成长的作品《追幸福的人》悄然登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
这部由祝捷执导、南吉领衔主演的影片,以真实事件为蓝本,用近乎白描的镜头语言,展现了普通人在命运重压下“向死而生”的韧性。
它不仅是一部关于个体挣扎的影像记录,更折射出中国文艺片在主题表达、受众共鸣与市场定位上的复杂处境。
一、真实与虚构的互文:纪录片的灵魂与剧作的肉身影片改编自导演祝捷对陕西汉中一个脆骨症患儿家庭长达十年的纪录片跟拍经历,片中患病女孩茯苓由真实患儿吴玉玲珑本色出演。
这种“虚实共生”的创作手法,既保留了纪录片的粗粝质感,又通过戏剧化重构赋予故事更强的叙事张力。
例如,主角巧巧(南吉饰)从工厂女工到北漂母亲的转变,既是对原型人物丁巧的提炼,也是对城乡迁徙浪潮中千万女性命运的浓缩。
当镜头扫过深圳工厂的流水线、北京城中村的隔断房、汉中老家的泥泞院落时,观众看到的不仅是巧巧的生存图景,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无数“巧巧们”的集体记忆。
导演刻意避免对苦难的过度渲染,转而通过生活细节堆砌真实痛感:女儿茯苓第八次骨折时巧巧颤抖的手、城中村拆迁时散落一地的廉价玩具、丈夫天冬(梁戟饰)开长途车时布满血丝的眼睛……这些碎片化的日常,构成了比戏剧冲突更尖锐的生命叩问。
二、女性叙事的多重突围:从“被凝视”到“自我赋权”南吉饰演的巧巧,是中国银幕上少见的“非典型女性形象”。
她既非传统苦情剧中逆来顺受的牺牲者,也非都市剧中光鲜亮丽的独立女性,而是一个在生存夹缝中野蛮生长的普通人。
从被迫辍学打工、意外怀孕到成为罕见病患儿的母亲,巧巧始终处于被动接受命运的状态,但她对幸福的追寻却展现出惊人的主动性:在女儿骨折后坚持用三轮车接送上学、在出租屋被拆时带着全家“像候鸟一样迁徙”、甚至在田间劳作时哼唱走调的情歌。
这种“不出走的反抗”颠覆了女性叙事中常见的“逃离-觉醒”范式。
正如南吉在首映礼所言:“如果说《白鹿原》的冷秋月是被封建礼教扼杀的悲剧,那么巧巧的不认命,则是用最朴素的生存智慧对抗结构性困境。
”影片通过巧巧与女儿茯苓的共生关系,完成对母职神话的解构——母爱不是天然的神性,而是在无数次崩溃与重建中淬炼出的凡人勇气。
三、文艺片的困境与可能性:在市场的夹缝中点燃微光作为一部全国艺联专线发行的影片,《追幸福的人》面临的挑战颇具代表性:一方面,其真实细腻的底层叙事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收获赞誉(南吉凭此片获亚洲新生代最佳演员);另一方面,豆瓣上“节奏平淡”“缺乏戏剧高潮”等争议,暴露出文艺片与大众审美的错位。
这种割裂恰是中国文艺片市场的缩影:当商业片用特效与爽感满足观众的逃离需求时,文艺片却试图用生活的粗粝将人拉回现实。
但影片的突破亦值得关注。
艺术总监杨超(《长江图》导演)与祝捷的合作,将诗性影像与纪实美学熔于一炉:水墨风格的海报中,巧巧面部的裂纹与头顶绽放的烟花形成强烈隐喻;惘闻乐队创作的配乐《My Crime》在片尾响起时,压抑的情绪随音符迸发,完成从苦难到救赎的升华。
这种艺术表达虽显“小众”,却为市场提供了另一种审美维度。
四、超越个体苦难的社会寓言影片最深刻的批判性,在于揭示“幸福”概念的阶级性。
当城市中产将“幸福”等同于消费主义符号时,巧巧一家却在生存线上重新定义幸福:女儿能独立上厕所、丈夫结束异地打工、拆迁废墟里长出野花……这些微小的喜悦,构成对主流幸福观的无声反讽。
导演通过巧巧北漂与归乡的双重漂泊,叩问城乡二元结构下个体命运的无力感——无论是深圳工厂的流水线,还是汉中老家的泥土地,都不过是不同形态的生存牢笼。
结语:在错位的对话中寻找共鸣《追幸福的人》或许难以复制《隐入尘烟》的票房奇迹,但其存在本身已是一种胜利。
当商业片市场充斥着悬浮的都市幻梦时,这部影片坚持用镜头抚摸生活的褶皱,在绝望的土壤里播种希望。
正如片中那场卡车上的烟花戏:颠簸的路途、劣质的烟花、巧巧带着泪光的笑,构成了中国现实主义电影最动人的隐喻——幸福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无数个“此刻”的微光汇聚。
10 ) 关于林树林的一点思考
林树林,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三个字都有“木”,而“木”最害怕的就是“火”。
影片中出现火的镜头是林树林不经意用火烧了卷子,电影中有提到他是一个做题家,他当初就是通过一张又一张卷子成为了一名知识青年,见识到一个更大的世界。
而火烧卷子,何尝不是林树林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前半生。
路演和主创分享了个人的这个解读,导演表示这是他未曾设想的角度。
千人千面,正是电影的意义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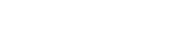





























追你妈的幸福
还行吧,不难看,但是没觉得在追幸福,觉得活的很苦。
根据纪录片改编而来,故事很生活化,家庭所遇到的困难也更真实!永远不要放弃继续前进的希望!没想到小女孩是素人本色出演,那种乐观坚强真的让人感动!
3.5,整个故事似乎像好几个做梦的片段拼接在一起。最后一段配乐很加分,立马就落泪了。
看过的人都会记住南吉这个优秀的女演员
以近乎纪录片的方式呈现“苦难”生活,但却没有刻意卖惨,而是以极平淡、极简化的平视视角刻画生活,很多时候让人忘却摄影机的存在,跟着影片中的人物共情,仿佛故事真切发生在自己面前一样。南吉这次表演有很大突破,简单质朴却又不失真。喜欢每次烟花燃起的声音设计,以及一些隐喻和意象,值得细细品味。@万达CBD
又一部类苍山的电影,刚开始还以为新秋菊(妆造)打官司结果又是和之前看过的苍山类似的苦情戏。
是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部好作品!是的,是一部应该拿奖的作品!在一个气温15度湿冷且沮丧的雨天,取完票走进空空的8号厅。一个人坐在电影院最后一排的中间独享了整部电影…直到惘闻的音乐作品片尾曲…直到字幕全部结束…
@万达cbd首映 只有现实世界才会缺少起承转合,悲剧叠加悲剧。导演说把纪录片拍成电影,是想让大家从惨淡的现实中逃离,至少带来一点希冀,但这两个小时太苦了,当悲剧被浓缩萃取,我们只盼着哪里能冒出一点点生命力,或许在菜地,在车顶。
有些段落看着太难受了 日子实在苦 听惘闻的配乐实在没绷住
幸福在哪?
人物的内心在哪里?非线性叙事的意义在哪里?
有时候看不清脸,谁是谁。插叙。堂姐妹说的方言好像不一样?
得益于导演多年的纪录片拍摄经历,影片以一种现实主义视角展示出底层生活的粗粝与诗意。大量手持跟拍与中近景镜头营造出生活中的真实:雾气氤氲的狭小浴室、女儿拐杖上缝补的旧衣片、丈夫永远不曾刮的胡子,这些细节构建出刺目而真实的生活肌理。同时影片的光影运用尤为惊艳,多处使用暗影中微弱光源,既隐喻命运无常,亦暗藏生命韧性的微光。 听说女主为了演绎这一角色特意增重近40斤,但稍显浮夸的表演导致她与角色原型显露出距离感,并且在角色内在复杂性上的探讨还有待加深。另外,影片对真实事件的还原近乎执拗,却因叙事焦点的涣散陷入平淡——女儿病痛、婚姻裂痕、城乡迁徙等议题如浮光掠影,缺乏戏剧张力的凝聚。当巧巧最终在大车轰鸣中奔向“幸福”时,过于工整的意象化收束,反而稀释了现实痛感的余韵。
2022年来自H! Market的项目。符合国产剧集标题越积极向就越苦情的不成文规律,女儿的病、双亲的死亡、工作的不顺利…一个接一个的打击会让人惊讶会不会太过了,但当最后的揭示有真实一家存在后,会稍微抵消这种感觉;对置身其中的角色去如何做出最终选择以及挣扎的挖掘都算细腻。女主的厚刘海+“巧巧”好似看平行宇宙的涛演了一部电影,对着女儿怒吼的“深圳生活开车...”也穿越麦琳。
有爱就有幸福
惘闻配乐多加了一星 特别平淡 普通人的生活
看过~
近乎纪录片式呈现了一家四口尤其是母女的辗转生活,没有通过诉苦的方式为罕见病患者这类少数人、少数家庭拉开一个了解他们的渠道;想起天才捕手计划,邀请患者家属书写的故事以至成书《孤独的病人》,少数人也值得被看见、被理解。期待导演的纪录片《玲珑》早日结尾、早日上映。
一个没有歌颂苦难,没有落入俗套的故事。